最近看日推的勤奮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雖然說我從小就是福爾摩斯跟亞森羅蘋的粉絲,可是長大後卻幾乎是英美推理小說的絕緣體,怎麼樣都無法進入那些由硬漢老婦情報員所構成的世界,反倒是對於日本推理小說,一直讀得津津有味。我在想,這是不是因為推理小說的謎題與推理其實帶有一定的「社會建構」,所以如果無法與作者分享同一個基模工具箱的時候,就無法進入小說的世界。
最近讀的幾本小說特別給我這種感觸。
在書的前四分之三,土屋設了一個極為精巧的「雙重密室殺人事件」;不只案發地點是密室,就連兇手當時也身處密室。而且,就算讀者得到近乎完全的資訊與暗示,也沒有辦法識破土屋所設計的詭計。這可說是本格派作家長年與讀者鬥智下的驕傲吧。可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門被推開的那一刻,所得到的閱讀樂趣,也才會如此的多啊。(笑)
可在書的後四分之一,土屋藉著兇手自白,嚴厲的控訴了少年法、人權團體,甚至廢除死刑的「鄉愿」與「縱容」。我們不知道,在現實社會裡,土屋本人是否是主張修正少年法,或是反對廢除死刑,但我們的確難以否認他字裡行間所明白陳述的觀點。即使這部份已經直白到不是文學了。
而說到文學,恐怕再也沒有像伊坂幸太郎那麼文青的推理小說家了吧?(笑)
 剛開始看《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想說,啊,日推界也有走村上春樹路線的人哩,這過去與現在兩條線的交錯,怎麼看都是一本恰巧跟推理扯上邊的文藝小說嘛。可是,就在我們因為「還沒有」人被殺死,而像那對寵物殺手毫無興趣的警察一樣,對事件漠不關心時,我們卻已經被「身分」所蒙蔽,也因此落入兩條時間線裡的詭計裡。到後來我們才發現,啊,原來這是一本這麼哀傷的小說啊。
剛開始看《家鴨與野鴨的投幣式置物櫃》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想說,啊,日推界也有走村上春樹路線的人哩,這過去與現在兩條線的交錯,怎麼看都是一本恰巧跟推理扯上邊的文藝小說嘛。可是,就在我們因為「還沒有」人被殺死,而像那對寵物殺手毫無興趣的警察一樣,對事件漠不關心時,我們卻已經被「身分」所蒙蔽,也因此落入兩條時間線裡的詭計裡。到後來我們才發現,啊,原來這是一本這麼哀傷的小說啊。
可我又覺得,在伊坂那近乎戲謔的文字與幻想的情節背後,其實隱藏了他的推理小說觀,那就是:虛空的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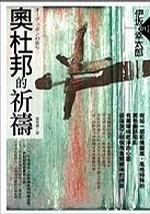 比方說,在《奧杜邦的祈禱》這本小說裡,從故事的內容來看,這是一本超現實的魔幻小說,但正因為如此,伊坂把我們帶進推理小說的極端(或者說,本質),那就是「推理的過程」。這是一本建立在許多推理小說後設語言上的推理小說,關於邏輯、為什麼、兇手、動機、事件線、名偵探,甚至悲劇性,都是它所企圖碰觸的。於是,看起來不像推理小說的小說,卻給我們最有趣的推理過程。
比方說,在《奧杜邦的祈禱》這本小說裡,從故事的內容來看,這是一本超現實的魔幻小說,但正因為如此,伊坂把我們帶進推理小說的極端(或者說,本質),那就是「推理的過程」。這是一本建立在許多推理小說後設語言上的推理小說,關於邏輯、為什麼、兇手、動機、事件線、名偵探,甚至悲劇性,都是它所企圖碰觸的。於是,看起來不像推理小說的小說,卻給我們最有趣的推理過程。
可是,在這有趣的推理過程中,伊坂卻透過伊藤與優午的對話,重複著一個對於「推理」的根本質疑:就算找到兇手、知道答案,那又如何?一切業已無可挽回啊。這旋律具體的透過伊藤的口說了出來;「這是一個邁向悲哀的結果。」
老實說,我很驚訝在伊坂的第一本小說就看到他這麼後設地先解構掉了推理小說的社會性,這也讓我好奇他之後的小說是否也帶有同樣的性格。而如果說,一個作家的第一本作品預表著他寫作的初衷與原點的話,那《影子的季節》這本書無疑是橫山秀夫的原點。
對橫山來說,所謂密室,並不是一個物理性質的空間,而是一種狀態;一種外界無法看透的狀態。而橫山小說中最常出現的「組織」二字,無疑就是他所建立的密室。外界無法理解的組織、自有內部運作邏輯的組織、兇手不會是外人的組織、沒有人可以逃離的組織(例如:《震度0》與《登山者》)。這樣的密室觀,無疑是極具日本特色的。
於是我深深地著迷於日推的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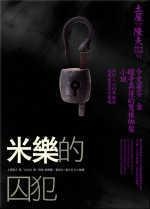

Comments